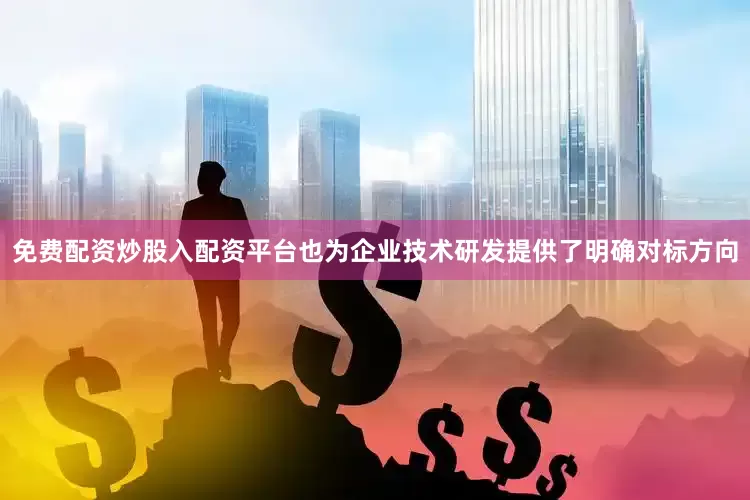美国空军大学教授张晓明在其专著《中越军事冲突1979-1991》(2015年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出版)中指出:
“由于部队长期没有参与实战,广州军区的前线指挥所特别安排了曾参与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、援越抗美战争及中印边境战争的老军官进行系统整理与统计。通过组织这些曾经的战士亲自讲述他们的战斗经历,部队开展了深入的战前教育。解放军一直坚持指挥员靠前指挥的传统,其目的是让官兵感受到指挥员始终与部队并肩作战,共同承担艰难和荣光。许世友将军在派遣参谋人员支援各军团工作之余,强调军、师、团三级指挥所必须派遣副职指挥员深入到更低级别的单位,以确保指挥链条顺畅,并且加强作战指挥的有效性。”
所谓“加强指挥”,实际上是指上级指挥员亲自下到下级单位协助指挥。在我军历史和传统中,副职指挥员下到更低级别单位进行指挥的做法是非常普遍的,而且在此次自卫反击战中,这一做法也显现出明显的特点。各军、师、团的领导干部普遍向前推进指挥位置,有些甚至深入前线的第三级单位。例如,各师常会配有来自军部的领导,团级单位通常有一至两名来自师部的指挥员进行指导,甚至营级指挥单位中也常常有团级指挥员的身影。根据广西方向第41军、第42军、第54军、第55军的统计数据,共有超过330名团以上的指挥员被派遣到各指挥单位,协助作战指挥。
展开剩余71%这一指挥模式经过实战检验后,既展现了优点,也显现出一些缺点。因此,战后关于这一做法的讨论异常激烈。支持者认为,经验丰富、指挥能力强的上级指挥员亲自到一线指挥作战,能够有效地指导战斗并鼓舞士气,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,对顺利完成作战任务起到了关键性作用。反对者则指出,上级指挥员的“协助指挥”有时会在关键时刻影响军区的决策,导致本级指挥员的意见被忽视。出现意见不一致时,最终执行的往往是上级的命令,结果本级指挥员的指挥权受限,甚至在战斗结果不理想时,责任归属也会发生混乱。
这两种观点各自有其合理性,但究竟哪种更为准确,需要从更广泛的角度进行具体分析与评估。
从积极的角度看,派遣具有丰富作战经验、指挥能力强且富有责任感的副职指挥员到下级单位,不仅能帮助年轻的指挥员更好地履行职责,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支持,也能够提升部队的士气。这样可以确保指挥的及时性与准确性,同时极大地激励部队,成为战胜敌人的关键因素之一。例如,第163师副师长李万余亲自带领第488团第3营突破至探垄,成功切断了敌军的退路,阻止了谅山敌军的增援。随后,他又带领部队圆满完成了攻占279高地、谅山市北区以及守卫奇穷河大桥北桥头的任务。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,第163师第3营表现出色,成功歼灭敌军1005人,创造了整个战役中步兵营击毙敌军的最高纪录。战后,中央军委授予李万余“能攻善守英雄营”的荣誉称号,广州军区也特意为他记了一等功。
另外,第121师副师长李培江在随军担任前卫的第363团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在作战中,李培江判断准确、指挥果断,他成功指挥前卫营在28小时内完成了任务,而团主力则用了32小时,顺利切断了敌军的3号A公路。这支部队成为整个高平战役中最早完成穿插任务的部队,李培江因此获得了广州军区授予的一等功。
然而,从消极的角度看,也有一些上级副职指挥员到达下级单位后,错误地认为自己拥有绝对的指挥权,甚至采取了包办代替的做法。这样一来,增加了一个指挥层级,反而影响了原本高效的指挥系统,导致了不必要的损失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第50军驻第150师工作组的指挥失误。
第50军第150师作为广西方向的预备队,按广州军区前指的部署与第41军配合作战。1979年3月6日,该师进入越南高平省扣屯地区后,按照部署要求需要在7天内完成多个任务:清剿残敌、搜查仓库物资、处理失散人员和烈士遗体等。为了加强该师的指挥,第50军派出了三位副军长组成工作组:关豁明、副军长刘忠和、副政委侯培聚,其中关豁明担任主导。
然而,这个工作组在指挥过程中屡次犯错。首先,工作组错误地选择了清剿回撤路线,导致部队陷入险境。之后,面对复杂的敌情和地形,他们过于自信,指令不合理,要求部队“只准前进、不准后退”,结果导致了敌军的猛烈伏击。更糟糕的是,指挥组没有及时向上级报告问题,错失了救援失散部队的最佳时机。最终,由于这些错误的决策,第448团遭受了惨重的损失,542人失踪,其中219人被敌方俘虏,此外还丢失了大量武器装备。这成为了十年对越作战中的最大损失之一。
此后,第50军返回成都后,成都军区对驻第150师工作组的处理非常严厉:关豁明副军长被撤职,侯培聚副政委受到党内警告,刘忠和副军长则降职并被调离岗位。
发布于:天津市瑞和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没有了
- 下一篇:伯乐配资介绍了跨省域国土空间规划的创新探索